一、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众所周知,日本文学一个绕不开的主题就是生与死。星之泽这部小说前部分看似写华人作家学者徐达裕在迁途东京后,妻子与初恋女性位置颠倒始末的故事,似乎有点电视连续剧的味道,但是看到最后,感悟到作者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受到日本文学生死主题的影响,勇敢地挑战生死这个在汉族文化中还属于比较忌讳的主题。
主人公徐达裕在浅草寺庙前偶然遇到年轻的在日华人《橘子姐姐在东京的生活》小视频的网红橘子,酷似自己初恋女同学赵红霞,橘子也对徐达裕脱俗的打扮和儒雅气质吸引,在不可抗拒的量子纠缠中,橘子的母亲赵红霞与昔日初恋的同学徐达裕转山转水在摇身一变成为徐达裕义女的橘子牵连中,于耳顺之年相见于橘子的东京婚礼上。在短暂的婚礼滞留期间,他们彼此的生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交织和共享,甚至越过红线,成为超过有形无实的妻子,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共享精神交流与肉体的欢愉。
一股谁也解释不了的神秘力量,把他们引导到即将发生海啸的碧海中,个体的赵红霞患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人”,身体会慢慢僵化。已经随时准备结束自己即将变成“僵尸”的肉体,偶然的大海,让赵红霞在她期待的初恋徐达裕面前,迎来了突发海啸。看似海啸把赵红霞葬身在海啸高浪中,实则赵红霞永远地占有了徐达裕。这种量子纠缠的作用,竟验证了伟大的相对论及量子力学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的那样化为“幽灵作用”。
明明是因缘巧合他们应邀一起参加了一个联谊会采风团,活动中安排去的中央海水浴场,不可思议地、在这碧波荡漾的海中,在情人的眼前,赵红霞的意愿在毫无预警的一瞬间得于实现——天空下、大海中、高浪狂卷的海啸中、赵红霞如愿以偿突然消失在徐达裕近在咫尺的眼前,从此以后,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使徐达裕决绝地告别至今的一切,在人们忙乱于赵红霞追悼会后续聚餐前,悄然离开经营多年的家、离开青梅竹马的妻子、离开儿子儿媳、离开不久前才知道是自己亲生女儿的橘子、离开含在嘴里都怕化掉的孙子潇潇。
此刻,徐达裕的灵魂已经与升腾至天国的赵红霞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量子纠缠去了。最后的镜头是徐达裕乘坐在从东京飞往大阪的飞机里,在高维度中冥想。
作者星之泽把生命之重呈露在读者面前,并没有说为什么离开,离开后去哪里,这是作者的妙笔之一,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让读者进一步惊觉到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在生命之前,任何人间的俗事,都不足挂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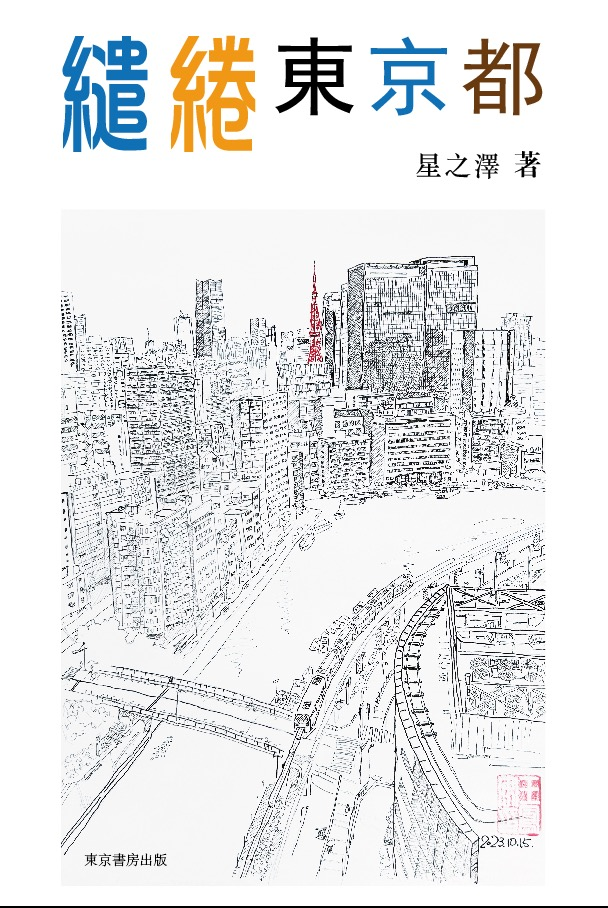
二、起笔于轻 落笔于重
好的作家,不光是写故事,还会在不经意之中,让我们从起笔落笔的艺术感,体会阅读的心情变化。这部小说第一个词,把主人公的名字亮出来:
徐达裕靠坐在从东京都飞往大阪府的航班座位上,飞机在上升的过程中突然颠簸起来,机翼做了两次大幅度上下摆动。邻座的几位女乘客惊恐地尖叫起来,刺耳的声音在机舱中回响。
这时,飞机播音器里传出亲切的声音:各位女士先生们,飞机遇到紊乱气流,请您系好安全带,不要在机舱里走动。
徐达裕神情自若,似乎没有被身边突发状况所干扰。他依然沉浸在近几年发生在自己与徐家的往事回忆中,好像一切的一切都与欧阳橘子作为义女走进徐家相关。
一下子亮出主人公名字,是典型的镜头聚焦主角的方法,让读者进入主角的思维、跟着主角的思维,迅速进入角色。
作者星之泽这一段是以轻松的一句“坐在从东京都飞往大阪府的航班座位上”开始的,但是紧接着用飞机的颠簸、甚至机舱内的尖叫,形成了叙述的紧张感,将读者带入了密闭而充满未知的空间,然后笔锋一转,第二个角色出场:“他依然沉浸在近几年发生在自己与徐家的往事回忆中,好像一切的一切都与欧阳橘子作为义女走进徐家相关”,引出了悬念。
一个既真实又有悬念的故事,在第一段就完成了人物、家庭、事件性的暗示,作者让记忆与命运交相呼应,织成一个网,预示了主人公徐达裕的家族故事的两个点和线,即徐家与欧阳橘子的命运。这个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两个点和线一经点破、竟是亲子。
这个沉重的结果,作者在小说的最后一段呈露出来,令人恍然大悟,这开篇是倒叙,起于轻,结尾再次落笔于沉重:“在候机大厅里,徐达裕踏上一架飞往大阪府的航班。舷窗外,夕阳落坠,残霞殷红。可是,徐达裕眼中出现的夕阳与残霞已经失去了别样色彩,只有一片黯暗。”
作者把家族命运的浮沉用飞机在高维度中的浮沉描写,最后让人惊觉到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三、借景手法、曲径通幽
小说结尾,另辟蹊径,用“借景造庭院”手法,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又凄美余韵的效果。当小说主人公徐达裕的初恋情人在海啸中,与徐达裕从近在咫尺、瞬间远在天边,一切过往的秘密,都在生命的消失中,反而变得清晰起来,往事不如烟,甚至更加挥之不去,终于徐达裕承受不了这生命之重,决意出走,他离开赵红霞的告别仪式现场,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家里。放弃与任何一个家人道别,只与家中鸟笼里的黄冠鹦鹉道别,制造了一种陌生感和戏剧性。原来这只鸟,是在这里起作用的。说实话当初我读到小说中这只鸟的出场,还觉得很突然,没想到作者赋予它充当最后的信使大任,方知作者的匠心伏笔啊:
徐达裕简单收拾一下衣物,把家里的每个房间打扫一遍。在客厅里,他看到了在长笼子里跳跃的黄冠鹦鹉,渺渺。
徐达裕走近鹦鹉,说道,渺渺,爷爷要离开家了。
鹦鹉说,我去,我去。
……
徐达裕有些沮丧地说,渺渺,爷爷要到很远的地方,不带你去。
鹦鹉说,很远的地方,不带你去。
徐达裕说,潇潇不去,他和你玩。
鹦鹉说,潇潇不去,他和你玩。
徐达裕更正说道,潇潇是和渺渺玩,不是和爷爷玩……不和你说了,爷爷走了。
鹦鹉说,爷爷走了,爷爷走了……
黄冠鹦鹉说完话,在笼子里扑打着翅膀,边叫,边跳,想冲出笼子,叫声中带着一种惶恐不安……
作为一家之长的徐达裕,也许这样毫无交代的离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姿态,但是作者的这个处理,让读者在充满意外的同时,丰富了想象的空间,让读者与作者一起完成每个人心目中的结尾,又未尝不是小说的精妙之处呢?
我想象当黄冠鹦鹉口中惊恐地叫出:“爷爷走了、爷爷走了”,那将是这个家庭天翻地覆的瞬间,这样的想象空间,是残酷的也是文学的。(2024年12月15日星期日于日本桑名望海厅)
|